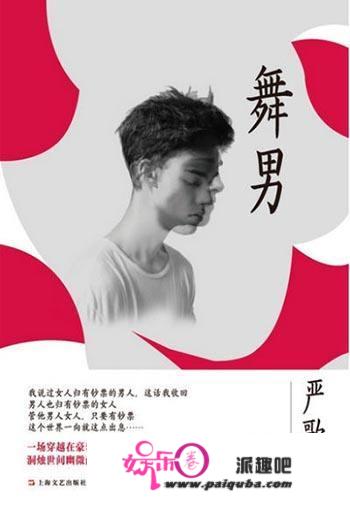严歌苓和张爱玲比较,谁更胜一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张爱玲和严歌苓各有千秋,应该说很难将两个人分出绝对的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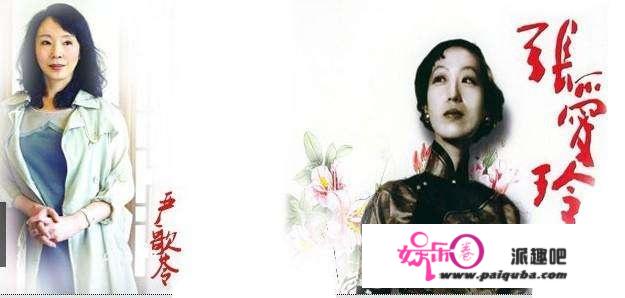
张和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出生在上海,都有国外生活经历,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都有一个外国丈夫,都是细腻的女性写作,都高产,都参与过很多影视戏剧创作,都被导演青睐,都是面向市场的写作,都有许多忠实读者,都获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都有某种局限和重复存在。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在张爱玲身上可能更适用一些。了解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张爱玲那份骨子里的“冷”,所以她作品的底色基本上都是绝望的。张爱玲的冷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而非单纯为创作表达而生成,所以一切人和事都在她笔下都于平淡处见苍凉,不需要对题材、故事做非常特意的设置。严歌苓就不同了,她的性格、经历和张爱玲完全不一样,她缺乏本性上的失望和决绝。她作品里的苍凉之色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索,很多时候需要借助背景、人物、情节的戏剧化设置来支撑。即便如此,严歌苓依然显得华丽有余、苍凉不足,这一点我曾经和王德威先生交流过,他同意我的看法(王德威:这是我尊敬的作家,但是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看法,她的作风是非常华丽,没有苍凉,大概《陆犯焉识》是我觉得我读过最精采的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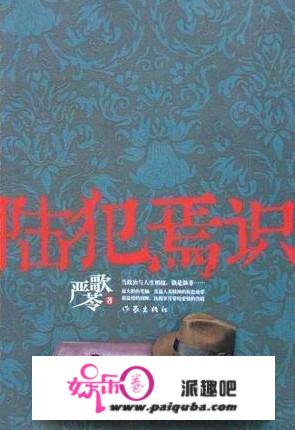
也因此,张爱玲的文字要比严歌苓更狠,往往寥寥几字就尖锐入里。
从故事上看,严歌苓的小说更多具有传奇性,这是她的表达需要决定的,更是她长期形成的一种写作套路。严歌苓喜欢称自己为“写稿佬”,早年在部队担任创作员,后来又到好莱坞学习和从事编剧,这两段写作经历本质上都是模式化的写作。她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两者杂糅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书写习惯:人性打底,人格英雄担任主角,其他角色服务于“三突出”原则。这样的故事注定好看,所以严歌苓作品无论在阅读层面,还是影视改编层面都非常受欢迎。但这种写法的主观设定痕迹相对较重,故事更像是一段传奇,而非生活。这一点同样被王德威先生认可过:“她的苦难其实是张扬的,她把这个苦难传奇化,那么我们也许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吗?”这一点在张爱玲那里就弱掉很多了,虽然她的一本小说集取名就叫《传奇》。除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意识先行比较明显,张爱玲的其它作品基本都是生活化的,甚至脱胎于自身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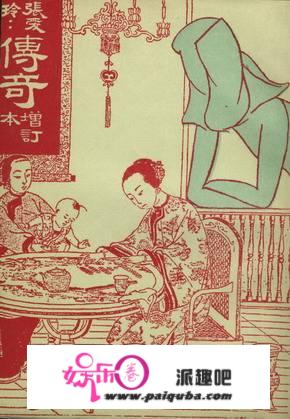
如果作家算是一种职业的话,严歌苓显然是要比张爱玲更职业化的。张爱玲基本还属于文人式的写作,虽然也有谋生的考虑,但相对而言随意一些,也和生活融为一体。严歌苓则是每天有固定时间进行创作的,时间之内全神贯注,时间之外该干嘛干嘛,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
这同时也决定了两个人在选题上的差异。张爱玲更多从自身出发,所涉相对比较狭窄。严歌苓则尝试各种题材,做职业化的处理。所以严歌苓的作品,既有《灰舞鞋》《芳华》《陆犯焉识》这种取材于自身或祖辈经历的,也有《扶桑》《第九个寡妇》这种非亲历的历史背景的,还有《老师好美》《舞男》《妈阁是座城》这些当今时代不同领域的故事。即便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严歌苓也不会拒绝接触,她会进行材料收集、调研考察、亲身体验,让自己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动笔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