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思维《悲剧的降生》尼采
《悲剧的降生》贯串全书的是对日神式思维和酒神式思维的思辨。要理解那部著做,核心就是大白尼采对那两种思维的论述和偏向。日神、酒神,是尼采借用古希腊人的神祗所寓指的不雅念。尼采大要认为古希腊悲剧是酒神倾向的典型表示,一种从“自我”中解脱出来、让任何小我意志和小我欲望连结缄默的艺术,那种艺术能使人在扑灭中遗失个别的概念,在集体的狂酔衬着中高呼“我们相信永久的生命”。那种悲剧的魅力源于对生命的忠实,对原始欲望和恐惧最逼真的体悟和认可,悲剧里洋溢的酒神思维让人勇于曲视痛苦,并在痛苦中获得欣慰。酒神思维是旷达的,狂野的,是一种英雄式的悲壮,好像为人类取火不吝受秃鹰撕啄之苦的普罗米修斯,又好像解开斯芬克斯谜语却难逃弑父娶母命运的俄浦狄斯,他们的个别扑灭的悲剧成就了一种超越个别的壮美。在我看来,尼采早期非常推崇的那种酒神式思维,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哲学不雅,他反基督束缚反理性主义以至反常识系统,倡导的是必定人生、必定生命,而酒神思维里表现的那种人类深层躲藏并将涌动发作的激情、欲望、狂放、恐惧、抗争,无一不在他意识中变幻为生命的素质,尼采说“过度显示为实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极乐,从天然的心底里诉说自我”。
因而,日神做为伦理之神,其要求的那种倡导适度和个别边界,并将自命不凡和过度视做“怀有敌意的恶魔”的日神式思维,在尼采眼里,成为不折不扣的褒贬对象。而诠释日神式思维更好的蓝本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他的哲学逃求沉着思索和逻辑辩证,崇尚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常识,其审美的更高法例是“万物欲成其美,必合情理”。以他思惟为代表,尼采总结为人类的理性乐不雅主义。而苏格拉底声称“美德即常识;蒙昧才有功恶;有德者常乐”,则被尼采认为是扼杀悲剧的乐不雅主义三大根本形式,因为“美德和常识之间、崇奉和道德之间,一定有一种一定的、可见的联合”,而悲剧在那种联合中被简化和公式化了。循着尼采的思绪,我理解为,日神式思维将人类“装扮”得异常elegant,籍由外化的繁文缛节使人丢弃内在的宣泄,从而接近个别的“伊甸园”。日神式思维强调个别,个别是日神关心的对象,因而日神倾向美化而非扑灭,是一种乐不雅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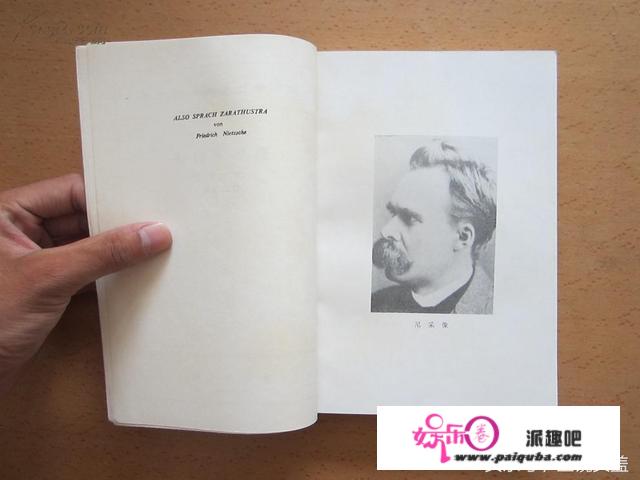

然而尼采觉得,那种苏格拉底式的乐不雅主义是懦弱的。试图通过因果律来探寻万物最内在的素质,必定是一种妄想。我不敢简单地将尼采的那种概念视做不成知论,但明显的是,尼采对常识是不推崇的,对僵死的、机械的一切教条抱有深入的思疑,他不认为那些能于痛苦中拯救人类。尼采眼中的悲剧文化恰好相反,"悲剧文化的重要标记是,聪慧被移到常识的位置上,成为更高目的,它不受常识诱惑误导的棍骗,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世界的总体形象,试图在那总体形象中,以爱的同感情把永久的痛苦理解为本身的痛苦"。所以其时的尼采,当机立断地视叔本华和康德为英雄,是挑战“隐藏在逻辑素质中的乐不雅主义”的屠龙者,他狂热地高呼“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屠龙者的勇敢程序,他们以傲岸的冒失,关于所有乐不雅主义的懦弱教条不屑一顾,以便完全彻底‘坚决的生活’!”
带着酒神思维的尼采,在悲剧中挖掘出属于他的神仙世界,同时也是他的艺术不雅。谈尼采,恐怕不克不及分开艺术那个词。尼采一心想通过艺术来拯救人类,他很早就声称“只要做为审美现象,世界的保存才是有充实理由的”。尼采描述的悲剧中的歌者,既是表演的成员,更是表演的独一实正的“不雅寡”,他将此归纳为戏剧的原始现象:看见本身在本身面前变形,如今举手投足仿佛实的进入了一个身体,进入了另一小我物。那种膨胀着生命力的表演,无疑给尼采看到希望,他本身早已沉醉在那种“酒神的兴奋”中,他在悲剧里寻找到那近乎迷幻的极乐,他的审美妙突然变得简单至极,他写道:一小我只要有才能不竭旁观一场生动的游戏,不竭在一群鬼魂的包抄中生活,那他就是诗人;一小我只要觉得到改动自我,有要到他人身体和灵魂中去向外说话的欲望,他就是戏剧家。因而,欧里庇得斯的“非酒神意向”式的悲剧,是无法获得尼采的认同的,那个被视为苏格拉底联盟的人将悲剧效果改换成日神式的戏剧化史诗。尼采说“实正的艺术家一定会有的一个特征,他对一定的套路几乎藏而不露,让它做为偶尔事务呈现”,所以他觉得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那种一起头就在仆人公自述里就明示了全剧摆设的做法是非常愚笨的,那种在戏剧中一碰到危难就有“天神得救”的大团聚结局是多么好笑,他不成以承受那种对悲剧的谋杀,他以至不认可那是艺术。
在尼采的艺术世界里,音乐有着非统一般的地位。尼采在书中对音乐的推崇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得强烈。尼采认为,音乐是有别于一切具象的工具及一切概念,虽然概念是曲不雅笼统得来的形式,但尼采仍然认为那是“事物上剥下来的外壳”,是外在的、外表的。而音乐,是“最内在、先于一切形态的内核或万物的核心”。那能够解释尼采为何不喜好后来的歌剧,因为歌剧中言说胜于音乐,从而没有了哀歌式的痛苦,而有苏格拉底式的美妙田园诗倾向,所以“歌剧是理论之人的产品,不是艺术家的产品”。在尼采的哲学中,音乐是生命的间接理念。
其实尼采的哲学及尼采的概念,我有赞成的部门也有良多不赞成的部门。但不克不及承认的是我在他的书中获得了思虑。现实生活中,我可能被一些人认为不乐不雅,但我仍然无法明晰界定什么叫乐不雅主义和灰心主义,正如我认为本身倾向日神思维的同时,也神驰酒神思维。关于《悲剧的降生》中关于日神主义和酒神主义揉合的讨论,我是看不懂,也领悟不了,所以也不在本文中论述。但我想,彻底的乐不雅和彻底的灰心也其实不存在,现实中固然以日神思维做为主旋律,但两种思维其实也是互相影响的。我很赏识尼采对生命的推崇,对解开束缚的那种狂野的激动,以至“自我”于尼采也是狭隘的表示,他甘愿世人都选择在扑灭中接近天然,接近素质。我觉得那些思惟,关于我们那些在都会中过着营营役役生活的人尤其宝贵,试问,在精致中漠视,倒不如在粗俗中狂欢吧?当然,尼采忽略了人甚至生命其实都是复杂的,日神思维对协调人类群体活动至关重要,究竟结果,神驰太阳,没需要就要奔向太阳吧。所以,中国的中庸论永久都有市场。
但是,尼采末归是疯了,关于他那也许是个恰到好处的结局,好像那有着大爱之情为人类采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也许会喜好那个对他的比方吧。
其实,疯子的世界是不是就必然悲凉呢?只是我们无法理解罢了。




我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