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长安十二时辰》:假如我是张小敬……
这几年我已经很少追剧,不管是国产剧还是国外剧,不管是粗制滥造还是制造精良,都几乎不看了。以前看多了国剧的不接地气,这些年兴致发生转移,于是减少了接触。想当年学生时代还自诩为热爱电影的文艺青年,刚出来工作时还兴致勃勃地追着每年的热剧,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恍如隔世。
之所以重看,是因为最近有闲,而我又暂时没找到别的新奇爱好,于是就把以前的好剧拿出来重温一遍。何况像《长安》这样制造精良的剧作,本来就值得反复看看的。无论是剧本、演员、表演,还是服装、化妆、道具,甚至音乐、灯光、舞美,处处可见创作团队的专心。多方的共同努力,最终才为看众显现出这部远销海外的上乘之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新近才意识到的原因,那就是隐隐躲在我内心深处的“盛唐情结”。按照《易中天中华史》的说法,“安史之乱”是总共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帝制时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那之前,帝国的雄心是征服向外的;从那以后,帝国开始停下扩大的脚步,眼光和思维都逐渐回收,文化和民族性格也由此开始内缩。
于我而言,我始终想要真真切切地了解,我们为何时至今日都依然被称作“唐人”?当时作为“世界之都”的长安,究竟是怎样一派繁盛气象,怎样一番万国来朝?当时的人们到底怎么食饭穿衣?怎么居住行走?杨玉环到底怎样的艳,李太白又是怎样的狂?假如真有时光机可以穿越,我最想往的目的地一定就是盛世长安。
展开全文
记得看第一遍的时候,当时我最大的疑问就是:死囚张小敬为什么一定要挽救长安呢?当朝廷各方势力还在争权夺利窝里斗时,他在单枪匹马地跟反派周旋搏命;当他早就看清楚当朝者的荒淫奢靡时,他却仍要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我曾一度为此感到费解:非要拿命往逞英雄吗?
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一口一个“为了百姓”不过是巩固皇权的托词,他这种明明可以事不关己却硬要当仁不让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
张小敬并不想当英雄,也并非为了功名前程,不管是当初从军,还是现在守城,他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恪尽职守的守护者。即使当权派对他处处提防,即使戴着“办成了无功,办砸了有过”的繁重枷锁,他依然抉择不退。
对于那些能够做到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人,我向来只有钦佩;对于那些自身都难保却还心怀众生的人,我也只有拜服。你们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兄弟敬仰万分,但真的学不来、做不到。
我们这些蝼蚁草芥,能够侥幸在时代和世事的惊涛骇浪中全身而退已经要竭尽全力了,哪里还敢心存什么凭一己之力解救苍生的念头。不想做,也做不了。因此假如我是张小敬,最大的可能就是带着最亲近的人溜之大吉,至于保护苍生解民倒悬的重任,就留给那些在身在其位当谋其政,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吧。
幸好如今也不是千年前的时代了,一城的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假如真要穿越回往,让我看一眼盛世长安是可以的,小住几天也无妨,就当短期旅游,真让我长久生活在唐朝就算了,这点我非常清楚。
不像那些天天喊嚷着古代多好多好的“崇古派”,他们脑子不好使,还特殊爱妄想,你真把他们送回往,保证不出一个星期就都要哭着喊着要回来了。跟今天四海升平的时代比起来,长安的十二时辰再好,甚至历史上的任何盛世王朝,其实都不值一提。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如是我闻》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冷。
——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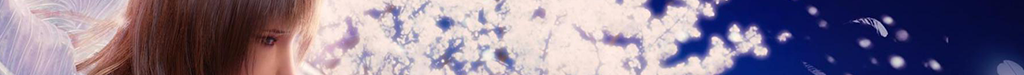

我来回答